“顶流”余华和他“鼻青脸肿”的青春

文坛“顶流”余华。
在中国作家圈,余华从来不是个“省流”的主儿。
就在今年4月间,他就至少上了2次热搜:一次是4月底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和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·库斯图里卡的对谈;一次是他给莫言的公众号投稿,但最终火的并不是那篇10万+的稿子,而是两个人的微信号都用的是小狗头像,一个憨态可掬,一个发型潦草,与各自的主人颇有几分神似。

网友制作的莫言和余华“同款头像”。
但在余华本人面前,这些都不过是浮云。聚光灯下的热度还没有散去,他就已经悄然转身,在海南过上了简单清闲的生活:白天整理文集,傍晚到海边散步,吹吹风、听听海浪,享受大自然的宁静。
今年3月,他为自己的成名作、小说集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再版,拍了一张海报。余华很喜欢这张海报,说它与作品的主题“一定要出去闯闯,哪怕鼻青脸肿”非常契合。“太有意思了,我自己都想买一本!我老婆认为挺好的,我儿子是‘90后’,他也认为很好的。”

余华很喜欢海报上“鼻青脸肿”的造型。
如今的文坛“顶流”,是怎么炼成“段子手”和年轻人的“嘴替”的?也许,答案就潜藏在他的创作原点里——与集子同名的短篇小说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,最初发表在1987年第1期的《北京文学》:十八岁的“我”带着“放逐”的心态开始了旅程,用一支烟换取了免费搭车的喜悦。车子突然抛锚了,“我”为了阻拦人们抢夺车上的苹果被打伤,但身为主人的司机却不闻不问,甚至最后还顺走了“我”的行李。小说讲述的,就是这样一个只有“我”受伤的世界的故事。
作品以寓言的形式,生动地描绘了年轻人初入社会的迷茫与挣扎,外在世界的荒诞与残酷,但同时也传递出一个积极的信息:只要保持内心强大、温暖,就能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宿。
新版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还特别收录了两篇余华的创作谈,这不仅是对原作的丰富,也为读者提供了一次与作家心灵对话的机会。
用海报上的话来说就是:看见余华“鼻青脸肿”的样子,我觉得我又行了!
01
真正的写作从“远行”开始
很多人认识余华,始于《活着》。实际上,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,还在浙江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做牙医的余华,就把所有的业余时间几乎都用于阅读和写作,目的就是一个——从卫生院调到县文化馆工作。

余华工作过的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。
1983年,他的短篇小说处女作《第一宿舍》在《西湖》杂志的第1期上与读者见面,接着《西湖》第8期又发表短篇小说《“威尼斯”牙齿店》。不久后,一个改变他命运的电话铃声响起,《北京文学》副主编周雁如邀请他赴京修改稿件。
那次北京之行,余华虽然充满了激动与期待,但立马想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——路费、住宿费谁来负责?结果杂志社不仅承担了所有费用,还按照干部出差标准提供了出差补贴,一天补助两块钱。这可让他高兴坏了,“其实,就算他们不承担,我自费也愿意去,因为那时我从来没有在大刊物上发过作品。”
到北京以后,编辑建议他把小说《星星》的结尾修改得“光明”一些。余华只用了一天就把结尾改好了,小说成功地发表在了《北京文学》1984年的第1期上。余华就此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海盐县第一个赴京改稿的作家。同时,《青春》杂志也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《鸽子,鸽子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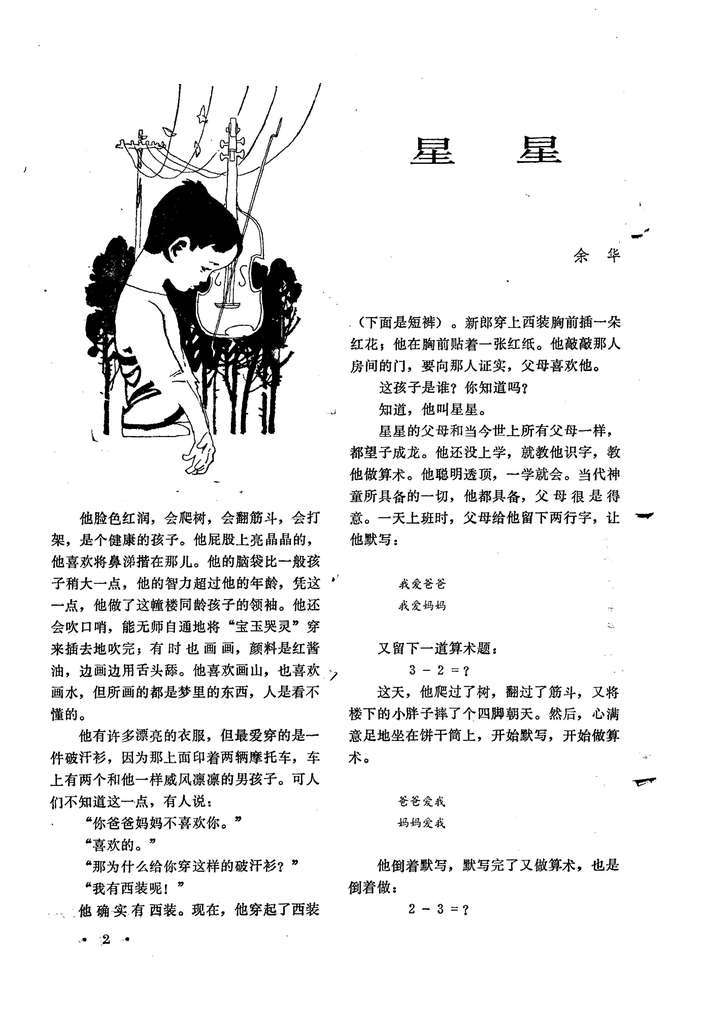
余华小说《星星》发表于《北京文学》1984年第1期。
在当了5年牙医、拔了1万颗牙后,他终于如愿以偿调到海盐县文化馆,成为专职作家。对于这段经历,他的感慨依然带着一股莫名的喜感:“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,可以说是赶上了最后一班车。如果晚两年开始写作,我可能就出不来了,现在还在医院拔牙呢。”
“我真正的写作是从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开始的,我把它看成我真正的小说处女作,因为之前的作品很不成熟。”余华说,小说的创作灵感,源于发生在浙江嵊州的一则新闻,报道了公路上一辆运载苹果的货车遭人抢劫的事件。“那时,这类负面新闻还相当罕见,这则报道让我感到十分讶异。”
至于他本人,在那之前的确有过一次出门远行的经历——也是在十八岁,搭便车去上海。“有个同学在学开卡车,他的师傅要去上海运货,我就搭了一个便车。结果,我们到的是上海郊区的一个工厂仓库,提完货就回来了,根本就没能见到上海市区。周边荒凉得还不如我们海盐县城。”
尽管如此,那次经历仍然令他印象深刻,小说中的主人公最终找到了“旅店”,而现实中的他,当时还徘徊在寻找的路上——对于写作初期的生活,他形容那是一段“相当艰苦”的日子:“白天在医院上班,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写。夏天时被蚊子咬,只能穿着高跟雨靴、牛仔裤写,弄得全身是汗。怕把稿子弄湿了,只能在手上绑上干毛巾。”

余华小说集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初版封面。
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是余华37年前写的。最近,他抽空又重温了一遍以前的作品,惊喜地发现其中有两篇小说挺满意的,一篇就是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,另一篇则是《鲜血梅花》,两者都以“在路上”为主题。创作后者的时候,他才28岁。言谈间,余华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:“令我惊讶的是,当时我在描述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时,竟然能够如此细腻地叙述并呈现途中的各种事物,我的文笔已经达到了我后来五六十岁时的水平。”
他坦言自己并没有将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之前的作品收录进去,是处于一点“要面子”的私心:“我希望人们一开始就觉得我是一个很厉害的作家,但那些评论家们真是‘坏得很’,非要把我过去那些准备阶段的习作也找出来。我其实希望他们能忘掉那些。”说完,他哈哈一笑。
02
“再伟大的作品都会有瑕疵”
作为新人,余华能坚持下来,离不开伯乐的鼓励。“当时的文学杂志编辑工作也非常认真,很多人会去读自由来稿,退稿还会附上铅印和油印的退稿单,上面写得工工整整的,开口就是‘余华同志’。”

年轻时的余华。
尽管经常被退稿,但余华说自己那时心态相当好,“我觉得被退稿也没什么,大不了这个杂志退了以后,往另外一个杂志寄。”到处“撒网”的结果是,余华对中国各地文学杂志了如指掌,连地市级的杂志他都熟知。他将这些杂志都视为投稿的目标,并摸索出一套“行之有效”的投稿方式:先尝试国家级的杂志,被拒绝了就转投省级,再被拒就投地区级的。“反正作品最后基本都发了。”
到了上世纪90年代,文学杂志的日子开始变得艰难,邮费上涨导致作者需要自己承担投稿费用,杂志社也不再退还自由来稿。余华的评价是:“现在的写作环境相比以前确实要好很多,但新人作家要出名却更难了。很多杂志都更倾向于向知名作者约稿,对自由投稿的关注度很低。”

余华早年出席文学活动。
有一点是余华自己也没想到的——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明显受到了卡夫卡小说的影响,他也一度以为,寓言、象征式的写法,将是他沿用一生的叙述方式。但在这之后,《活着》和《许三观卖血记》相继问世,他讲故事的方式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余华把作家分为两类:一类是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成熟的叙述系统的,每次写作哪怕是不同的题材,大体上都是同一种风格的不断延伸;另一类则是像他这样,每次都必须为一个新的题材寻找最适合的表达方式,甚至不惜打破已经趋于成熟的写作体系。
《兄弟》于2005年8月首次出版时,在国内引发了不少质疑,其实当时余华自己也不知道,下一部长篇小说会是什么样子。“我现在的写作原则是,当某一个题材让我充分激动起来,并且让我具有了持久的写作欲望时,我首先要做的是尽快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式,同时要努力忘掉自己过去的写作经验,因为它们会干扰我。”在余华看来,这就是他的作品总是不断在“变”的原因。
包括他对自己作品的评价,其实也在不断地推翻重来。《兄弟》刚出版时,这是他最满意的个人作品。又有一段时间,他最满意的是自己的随笔。

小说《兄弟》一度是余华本人最满意的作品。
可能唯一没有变的,是他喜欢“嘚瑟”的习性:“我现在读以前的作品,经常会感叹我能写出这么好的章节,真不可思议,我很羡慕我那个时代的才华。”
相比于莫言的一气呵成,余华更喜欢反复修改——在小说初稿完成后,会先放上一两个月,然后从头到尾修改一遍。之后,不论它变成什么样,他都会选择发表。有了电脑以后,他发现自己更喜欢修改了。“我经常会发现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,有些我会记住,但有些可能也就忘了。”
有时候,他也难免会对过去的一些修改感到懊悔。比如《兄弟》中李光头的梦中情人弹木琴,他一度把这个细节给删了。“虽然现代读者可能不理解什么是木琴,但这并不属于叙述问题。我之前把它删除其实是个错误。我觉得自己有时候过于面面俱到,甚至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。”
他坚信作品的质量取决于细节,而不是情节。“情节绕来绕去没有意义,莎士比亚的故事,情节几句话就能说清楚,有些复杂的故事读过之后反而很容易就忘记了。我只要能把握住结构和人物就行,细节我认为差不多都过关了,但疏漏是无法避免的。”“不要没完没了地改,因为再伟大的作品都会有瑕疵。”

余华在纪录片里讲述创作经历,并贡献了一个诗意的片名:《一直游到海水变蓝》。
03
与莫言的“相爱相杀”
余华鲜少涉足文学评论领域,唯一的例外是他为好友莫言的作品《欢乐》写过评论。“我比较爱读作家谈他们创作的文章,这些文字比评论家的文字要有意思。”他提到,像博尔赫斯、马尔克斯以及海明威等文学巨匠也撰写过评论,且堪称典范。“他们并没有因为评论写得好,就想成为评论家,我更没有这样的想法。”
余华与莫言曾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共读,他们不仅是同窗、同道,还当过室友,亲密到“共用一支牙膏”的地步。这可能是两个人后来连微信头像都像“情侣同款”的根源。

余华和莫言同框。
每次提到莫言,余华都不吝赞美:“一个作家如果缺乏创造力,那么无论其文风有多么华丽,都难以深深触动读者的内心。莫言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,所以我非常喜欢他。”
有一次,他们在电话里一起讨论《丰乳肥臀》的书名。“我第一次问他书名是真的吗?他回答说是的,我们在电话里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然后,我认真地告诉他,我觉得这个书名起得非常好,真的很好。”
莫言的《生死疲劳》问世时,余华亲临发布会现场,他坦言自己在阅读后心生羡慕,对莫言的创作才华赞不绝口。同样,莫言也格外青睐余华的作品,两个人经常在公开场合表演“商业互吹”或者“相爱相杀”。
去年5月,《收获》创刊65周年庆典在北京举行时,主持人用莫言的作品标题《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》,形容两人之间的关系。莫言当场“爆”出一段金句:“余华不是我的对手,他从来没有对我形成威胁。只有在鲁迅文学院,有一段时间,他老在我旁边写东西,笔摩擦纸张的声音太大声了,影响到了我的写作。”

莫言笑称“余华不是我的对手”。
莫言对自己近年来的总结是:头发越来越少,脑洞越来越大。有一次,余华在网上直播时,又一次提到《生死疲劳》。他说,莫言的小说写得太牛了,可回头一想,“他有才华,头发这么少”,似乎又找回了一点平衡。
后来,两人一块上综艺节目,回头莫言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《和老友们一起录节目好开心》,并提到了一件趣事:有人拿着余华的《活着》让自己签名,本来不想签,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决定代签,因为他写的“余华”,比余华本人写得好看。
近日,余华给莫言的公众号投了一篇名为《山谷微风》的散文,写的是他春节期间在三亚小住时“与风共舞”的独特感受。莫言特意加了一段按语《妙哉此风》,称“文章一如既往地显示了余华散文的幽默风趣以及精彩造句”,“微风里一般不产生传奇,但很可能产生爱情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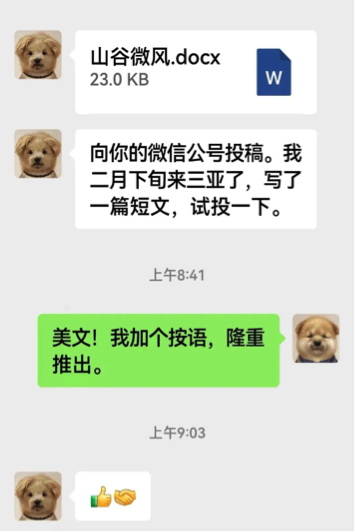
余华给莫言的微信公众号投稿。
04
在“卷”和“躺平”之间灵活切换
在创作道路上,余华特别感谢夫人陈虹。他说,陈虹是“最棒的读者”,总能在阅读他的初稿时,敏锐地捕捉到文中的精彩之处和存在的问题,并提出中肯的建议。现在家里边又多一个特别好的读者——儿子余海果,三人经常在一起搞“头脑风暴”,这经常会激发他的灵感,也帮助他的作品更加完善。
在写《文城》的时候,家里的讨论尤为激烈。在最后定稿时,他“恳求”家人不要再提意见,因为他已经改了十多遍了。《文城》这个书名也是得益于夫人的建议。“我夫人是诗人,她很敏锐。以前的书名叫《南方往事》,但我对这个书名不满意,后来她提议改成《文城》,我觉得改得太好了,和书里每个情节都对应上了。”

余华和陈虹(左一)。
在父母的影响下,余海果从高中起,就对写电影剧本产生了很高的热情。余华对此事的态度是“随缘”,“未来的路还很长,他可能会继续走这条路,也可能会选择其他的方向”。
至于儿子开始尝试写小说,余华则是既热情鼓励,又严格要求。“他写了几篇小说,我觉得写得相当不错,但陈虹觉得还需要锤炼。”如果儿子真的决定走写作这条路,他会尽力提供支持。“我最早开始写作时,就苦于我爹不是一个杂志编辑,而是一个小县城医生。如果我儿子要写作,起步比我肯定要容易得多,起码发表不是问题,我可以找关系。不过,我希望他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去发表作品,而不是靠关系。”
年轻人的成长历程一直是众多作家热衷探索的主题,余华也不例外。尽管今天的年轻人与他年少时所面临的环境截然不同,但是成长的烦恼与迷茫却是永恒存在的。
余华认为,每个孩子在成长阶段都会面临不同的挫折,这与他们的个性和经历紧密相关。“即使在一个物质条件优渥的家庭中,孩子内心的挫折感也可能与父母所想象的截然不同。”因此,他始终尊重儿子的选择和决定,希望他能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闯出一片天地。
他特别叮嘱儿子,要多读哲学类书籍,“我说如果你这个年龄不读哲学的书,你过了40岁以后就永远不会读了。多读哲学对你的逻辑思维和写作能力都会有很大的帮助。”

余华受访时谈笑风生。高佳馨 摄
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,余华经常和学生打交道,这让他对网络上流行的新事物时常保持关注,例如“卷”与“躺平”等流行词汇。余华并不觉得这二者就一定是对立的,“为什么要把‘卷’和‘躺平’对立起来?我觉得它们是互补的,你不可能永远‘卷’下去,但老是‘躺着’也很无聊。”
在他看来,这两者是可以根据个人心境和需求灵活转换的,他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。“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勤奋且有拖延症的作家,习惯写一写、歇一歇。当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时,如果被问到最近在写什么,很多人会说他们还没写完。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回答,因为这和我一样。我总是有很多未完成的作品,有短篇小说,也有散文。甚至我的长篇小说也是这样,一部没写完,我又开始写另一部了。”
在今天“出门远行”的年轻人当中,流传着这么一句话:“人生不是轨道,而是旷野。”余华的见解还是那么独特:“我觉得没有轨道,你是到不了旷野的……我们之所以走上轨道,是为了最后能够去到旷野。”
特约作者 高佳馨 南方+记者 郭珊
图片源于网络(除署名外)




